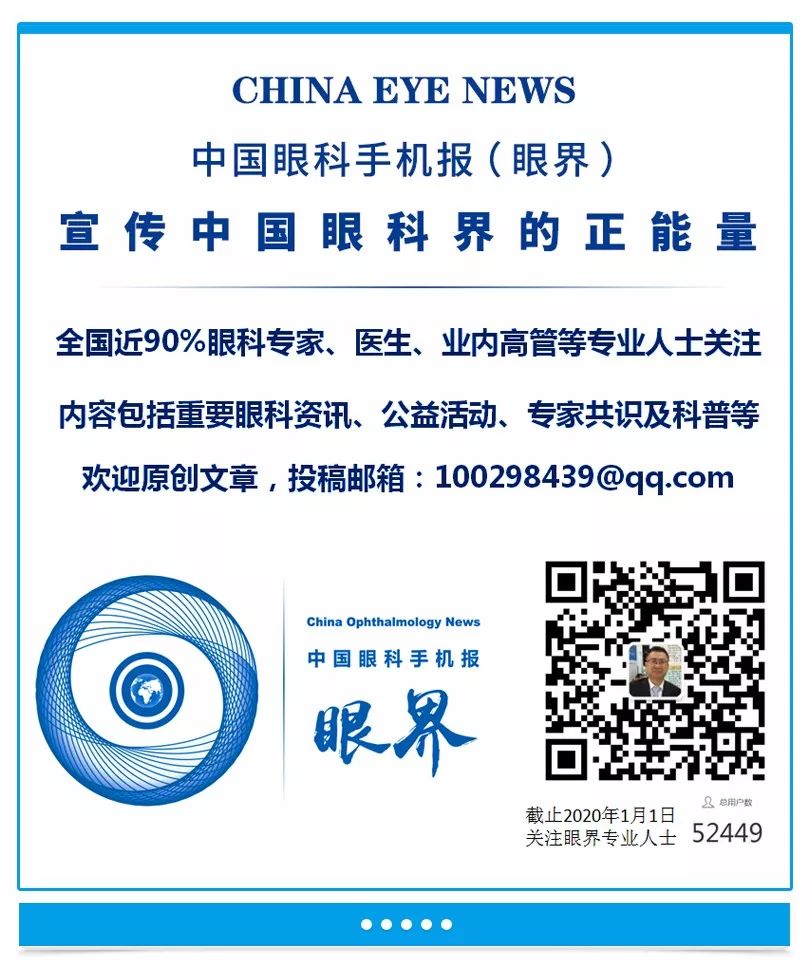国际眼科友人的中国梦系列栏目第一期
本期海外眼科专家 Ting(张书维), MD, PhD
本文特别致谢中山眼科中心张秀兰教授推荐并组织翻译
前言:在国外,有一些眼科专家对中国特别有感情,同时也会说中文。经专家建议,中国眼科手机报《眼界》现推出国际眼科友人的中国梦系列栏目。首期推出(张书维)医生,他是新加坡国立眼科中心的玻璃体视网膜专家,杜克-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副教授,及眼科人工智能( , AI)部门负责人。他目前还兼任中山眼科中心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科客座教授。

Ting(张书维)医生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美国-东盟富布赖特访问学者(US-. W. ,2017-2018),美国眼科学会AI工作组的创始成员,并在《》, 《 》,《 of of 》等多个学术期刊的编委会任职。迄今为止,他共发表论文140余篇,其中在《JAMA》, 《 》, 《 》, 《 g》, 《 》, 《 in and 》, 《 in and 》等杂志发表了与AI相关的论文30篇。在眼科AI全球化的大背景下, 作为第一作者与该领域的多位知名专家(包括 ,, , , Keane等)合作发表了2篇重要的AI综述文章,总结了AI研究的前沿技术、关键的技术和临床方面以及眼科AI的未满足需求和未来方向。
Ting(张书维)医生荣获多个奖项,包括视网膜创新研究奖(2020年),美国黄斑协会 奖(2019年),APAO青年眼科医师奖(2018年),APTOS青年创新者奖(2017年)等。实习期间,他在美国OKAP国际考试中名列第一(2012-2014年),获得奖(最佳总住院医师),在86名住院医师中他以荣誉致辞生的身份毕业于新加坡最大医疗机构。他最近还被眼科医生公认为眼科深度学习领域的顶级思想带头人之一。
以下为中国眼科手机报(眼界)对 Ting(张书维)医生的专访内容:
1、能否向我们介绍您的工作经历和研究方向?您在眼科人工智能或深度学习方面有什么经验?
我现在是新加坡国立眼科中心的玻璃体视网膜专家、杜克-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副教授和中山眼科中心眼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客座教授。在工作方面,我从事视网膜内科和外科疾病的诊断与治疗,如视网膜和黄斑手术、糖尿病性黄斑水肿、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视网膜静脉阻塞等。2017年,我作为美国-东盟富布赖特学者访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JHU)医学院和应用物理实验室,交流人工智能( ,AI)、大数据分析和远程医疗等领域的专业知识。2014年,我在西澳大学完成了视网膜成像和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光学工程的学业并获得博士学位。
迄今为止,我的AI实验室在多个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了AI论文30多篇,包括《JAMA》, 《 》, 《 》, 《 》, 《 》。以上成果离不开我的导师Tien Wong教授的鼎力相助,非常感谢他为我创建了很好的平台。作为AI项目的临床负责人,我分别以首席研究员和联合研究员承担了约150万和2500万美元资助的研究项目。我作为第一作者与来自世界各地的眼科AI专家共同发表了2篇重要的AI综述文章。目前我任职于4个杂志的编委会(, ,BJO,TVST),负责审阅AI和大数据相关的稿件。更令人兴奋的是,在2019年10月旧金山举办的美国眼科学大会( , AAO),我被委任为AI工作组委员会的创始成员。
2、请你可以简单的介绍下AI或者深度学习是怎么工作的吗?有哪些关键词是我们读者需要了解或学习的呢?
人工智能(AI)的概念最早形成于1956年在达特茅斯学院举办的一个研讨会后。“机器学习”(ML)一词后来由 于1959年创造,并指出"计算机应有能力使用各种统计相关技术进行学习,而无需明确编程"。利用机器学习技术,算法可以在受监督或不受监督的条件下,根据训练阶段已输入的数据来学习和做出预测。机器学习已被广泛应用于计算机视觉和基于复杂数学模型的预测分析等领域。随着图形处理单元(GPU)的出现、数学模型的进步、大型数据集和低成本传感器的可用性,深度学习(DL)技术出现,吸引了业界的极大关注并被广泛应用于相关领域。
深度学习利用多个处理层来学习具有多重抽象级别数据的表示形式。深度学习的方法可以使用完整的图像,并将整个图像与诊断输出相关联,从而淘汰了需要"手工设计"的图像功能。随着性能的提高,深度学习现已在图像识别、语音识别和自然语言处理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一个高鲁棒性的深度学习系统,必须要有两个主要构成组件——"大脑"(技术网络-卷积神经网络[CNN])和"字典"(即数据集)。卷积神经网络是由一系列处理层组成的深层神经网络,类似于动物视觉皮层的生物结构。它通过可导函数将输入数据转换为输出数据。Hubel和的研究发现视觉皮层中的每个神经元都会对图像中某个区域特有的刺激做出反应,这将激活视觉空间的特定区域,称为感受野。感受野聚合在一起,覆盖整个视野。在这个区域中可以找到两类细胞 - 简单细胞与复杂细胞。
从广义上讲,卷积神经网络可以分为输入层、隐藏层(也称为特征提取层)和输出层。而隐藏层通常由卷积层、池层、完全连接层和标准化层组成,并且隐藏层的数量因不同的卷积神经网络模型而异。训练和开发阶段通常将数据分为训练、验证和测试数据集。这些数据集内的数据不能重叠;在其中一个数据集(例如训练集)中的图像不得用于其他数据集(例如验证集)。理想情况下,这种非交叉原则应扩展到患者群体。并且应在所有数据集中保持目标条件的大类分布。
训练集:深度神经网络的训练通常分批(子集)从训练数据集中随机采样。训练数据集用于通过反向传播来优化网络的权重。
验证集:验证过程用于参数选择和优化,并通常也用于实现和执行训练的停止条件。
测试集:最后,应使用根据测试集选定的优化模型评估AI 算法的性能。应使用不同设备、不同人群以及不同临床环境中拍摄的独立数据集测试AI系统非常重要以确保AI系统在临床环境中的通用性。
3、人工智能有助于哪些眼科临床需求的实现?如何做到这一点?
到2050年,全球60岁以上的人口会从2015年的9亿增加到20亿,其中80%生活在中低收入国家。随着人均寿命的延长,人口老龄化速度远高于过去。因此,需要对许多眼部和全身性疾病,如糖尿病视网膜病变(DR)、青光眼、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和心血管疾病进行更长时间的疾病监测。人口膨胀也给儿童盲病(如早产儿视网膜病变、屈光不正和弱视)筛查带来了更大压力。例如,糖尿病患者需要终生监测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对于非洲这样每30万人口只有1名医生的国家,这根本是不可能的。因此,尽管AI技术的实际部署需要严谨的计划,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专家支持,其应用仍然可以显著提高筛查率。
4、在临床上AI部署的障碍是什么?技术局限性是什么,如何克服它们?成本是个大问题吗?
眼科学中AI研究和临床部署的潜在挑战如下:
首先,眼科AI算法以大量图像为基础。共享来自不同中心的数据是增加神经网络的训练输入数据量的一种显而易见的方法。但是,数据量的增加并不意味着网络性能的提升。例如,添加大量来自健康受试者的数据很可能对疾病分类没有帮助。此外,用非常大的数据集进行训练,可能会增加伪相关的可能性10。使用视网膜图像进行眼和全身疾病的预测和分类,需要清晰的指南来确定用于训练的最优数据量。
其次,当在不同中心之间共享数据时,需要考虑不同国家不同的隐私相关法律。尽管法律旨在保护患者的隐私眼科智能诊断系统,但有时会成为有效的研究计划和患者治疗的障碍。通常,图像和其他所有与患者有关的数据都需要匿名,并获得患者的同意才能共享。这需要包括数据存储、管理和分析的技术方案,其实施需要花费时间和成本。还需要硬件软件投入以及专门技术,并且劳动强度大。在数据共享上投入很困难,因为花费高,且收益不是即刻产生的。尽管如此,全球所有AI研究小组都应继续合作来克服困难,从而利用大数据和深度算法的力量来推进科学的进步。
第三,由于担心竞争对手率先发表新结果,数据分享可能受到影响。通常由于团队中较弱的成员害怕自身学术生涯受此影响,在机构内部也可能发生类似情况。事实上,资助方如大学或各种机构所定义的关键绩效指标,包括出版物数量,影响因子和引用指标,可能是有效数据共享的主要障碍。在机构层面上,完成与其他合作伙伴之间的协作协议是一个漫长而费力的过程,它会减慢对共享数据的分析。当涉及知识产权问题时,更可能迁延日久。这些涉及多家机构的协议,通常时间跨度为一年或更长时间。同时还有着其他速度更快团队的竞争,以及合作者对该课题失去兴趣的风险。
第四点,在训练集中,对于不同的疾病(如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青光眼和老年性黄斑病变),AI需要对大量的图片进行表型的确认。神经网络的能力取决于图像的数量以及数据具有的对于疾病谱的代表性如何。除此之外,算法在临床实践中的适用性取决于其对于疾病的表型分类能力和人类分级标准对于这套系统的拟合程度。
第五点,尽管对于青光眼、DR和AMD之类的常见眼病,已经有足够数量的图像来训练神经网络,但对于罕见病而言,因病例稀少,神经网络对于它们的判读仍是个问题。有一个方法是通过合成的眼底图来模拟罕见眼病的表现,然而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现有的手段无法证明其是有效的。再者,卫生主管当局是否能够批准这种数据并非来自真实患者的做法,还不得而知。但是,生成合成图像是一种有趣的方法,可能在未来有应用的潜力。
第六点,深度学习的能力不应被设计为与医生竞争的能力。神经网络能做到的是在规定任务中的出色表现。神经网络能够对DR进行分级,能够检测AMD的高危因素,但它不能替代视网膜专科医师。因此,将新技术纳入深度学习系统是很困难的,因为它将同样需要大量基于这种新技术的数据。同时,将新技术纳入基于分级系统的神经网络是一项耗时费力的工作。考虑到现有非常多针对水平扫描的新兴影像技术,包括血流OCT(OCTA)和多普勒OCT,这些技术将在眼病的诊断、分级、进展分析方面发挥巨大潜力,也成为了未来的重要挑战。
第七点,提供医疗保障在逻辑上是复杂的,不同的国家/地区的策略差异很大。将基于AI的解决方案纳入医疗保障的浪潮中是十分困难的,而且需要各方充分的联络沟通,也需要所有利益相关者(包括监管机构、保险公司、医院经理、IT 团队、医生和患者)的协同努力。执行这种策略必须简单明了,没有行政障碍才能被接受,迅速传播成果是另一个重要方面。将AI应用于临床实践的另一个重要步骤是形成一个现实的商业模式,这个模式需要充分考虑患者、医疗保健支付方和提供方的具体利益。在这个模式中,主要需要考虑的是回馈、效率和未满足的临床需求。这种商业模式也需要考虑长期影响,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AI的持续性连接沟通和学习能力,与提高在临床工作中的实用性相关。
第八,对于深度学习算法,尚缺乏伦理规定和法律法规。这些问题可能发生在数据源、产品开发和临床部署等阶段。Char等人指出,深度学习算法设计背后的意图也需要考虑。在医疗算法中建立种族偏倚时,人们需要小心谨慎,尤其是当医疗保健服务已经因种族而异的情况。另外,鉴于质量指标对公共评价和报销率的重要性日益增加,人们可能更倾向于设计深度学习算法,从而提供更好的性能指标,但不一定针对患者。传统意义上,医生能从患者的医疗记录中隐藏个人信息以确保其机密性。但将数字化健康档案和基于深度学习的决策辅助联合时,从电子化系统中掩去患者的病历信息将变得困难。因此,围绕这些问题的医学伦理或许需要随时间演化进步。
最后,AI系统对于眼病筛查应是廉价且高效的,因此,相比以上提出的挑战,这不应该成为AI发展的瓶颈。
5. 人工智能/深度学习于临床部署后,您预计可能需要多长时间才能看到来自患者方的反馈数据?
在新加坡,我们从2018年开始将人工智能系统整合到新加坡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综合筛查计划中(SiDRP)。我们希望能在未来3到5年内看到结果。对于青光眼、老年性黄斑变性和早产儿视网膜病变等疾病,虽然目前许多研究小组已经在各自的人工智能系统上发表了可靠的报告,但是相关算法的落地需要的时间会比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更久。
6. 人工智能/深度学习领域目前最令人兴奋的事情是什么?您目前有关注什么项目吗?
在我看来,人工智能/深度学习领域最令人激动的事情莫过于Arute等基于 AI发表的“量子物理学的发展”。它所描述的处理器可以显著提高数据分析的处理速度。对一个量子电路采样100万次,目前经典的超级计算机可能需要1万年,而它仅需要大约200秒(3.5分钟)就能完成。这项技术很可能在未来几十年内再次打破目前诸多技术和医疗行业的格局,将我们带到工业5.0时代。
7. 眼科人工智能/深度学习领域竞争是否激烈?如果有的话,哪些研究团队/国家可能首先取得成果?
当然有。因为有剑桥大学、帝国理工学院、多伦多大学、纽约大学、加州理工学院等世界一流计算机科学系的加持,美国、加拿大和欧洲的人工智能/深度学习发展一直处于全球的最前沿。在新加坡,我们也有幸拥有一支世界一流的技术团队,在眼科领域开发出许多很棒的算法。虽然新加坡只有500万人口,相比其他国家,它要小很多。但也正因为如此,它更容易创建一个强大的服务系统来支持人工智能算法的临床部署,例如将人工智能系统整合到新加坡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综合筛查计划中。
尽管如此,如果非要选择哪个国家可能首先在眼科实践中取得竞争力,我觉得非中国莫属。第一,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就数据而言,不是其它国家可以比的。第二,可能有人会质疑他们数据的可靠性。目前为止,在我看来,中国前五名眼科机构已经在包括人工智能在内诸多领域都处于世界一流水平,并且许多中国临床医生在很多方面都被低估了。在我最近的中国行中,我对中国临床医生在眼科人工智能和数据科学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感到相当震憾。第三,中国政府非常支持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融合人工智能的社会。因此,对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相关项目的研发提供了很多的资金支持。目前,已经有许多实时人工智能集成算法部署在临床领域眼科智能诊断系统,这也是我认为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可能领先的原因之一。但是,由于语言的影响,他们一些先进的研究成果不一定能及时地被高影响力的医学期刊接受。
8. 开展这些技术时是否存在过伦理争议?这些技术将对全球的眼科医疗产生怎样的影响?发展中国家是否必须“迎头赶上”?发展中国家是否需要先开展一些其他的部署?
目前,人工智能在医疗领域的应用引发了广泛的伦理争议。对于发展中国家,我认为人工智能在加速医疗标准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力,尤其是在缺乏眼科权威专家的国家。但是,人工智能的临床开展离不开远程通信、IT基础设施/平台、IT专家和医疗专家(医生)等的支持。因此,有必要先完成这些方面的部署。
9. 开发算法时某些人种的数据是否受到“青睐”?如果是这样,这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此问题有什么解决方案吗?
AI算法通常是在美国/欧洲这样的发达国家开发的,这些国家有很多白人,而在亚洲(例如新加坡),我们的人口由中国人、马来人和印度人组成。鉴于AI算法的开发可能基于某些人群样本,因此测试算法的外部适用性很重要。
10. 如果出现问题,伦理问题如何处理?谁应该负责:生产者、算法开发人员还是医生?
这个问题我们目前没有很好的答案。我个人认为,我认为医生应该是最终的负责人,如果AI软件给出了错误的诊断,则他们有责任修正诊断。许多报纸头条和研究报告称,人工智能的性能可能比人类更好,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是正确的。尽管如此,在医疗保健方面,我始终认为医生应该成为把关所有不同健康技术的评估和应用,以提高医疗水平。应根据患者的临床表现和检查结果做出临床决策。应该始终将AI视为辅助工具,而不是将其作为医学诊断的唯一决策工具。此外,在采用任何AI软件之前,医生还应仔细评估文献中所有证据,就像新药上市前的评估一样。
11. 如果将AI用于分析结果/图像,是否有可能增加转诊次数?世界卫生保健系统能否应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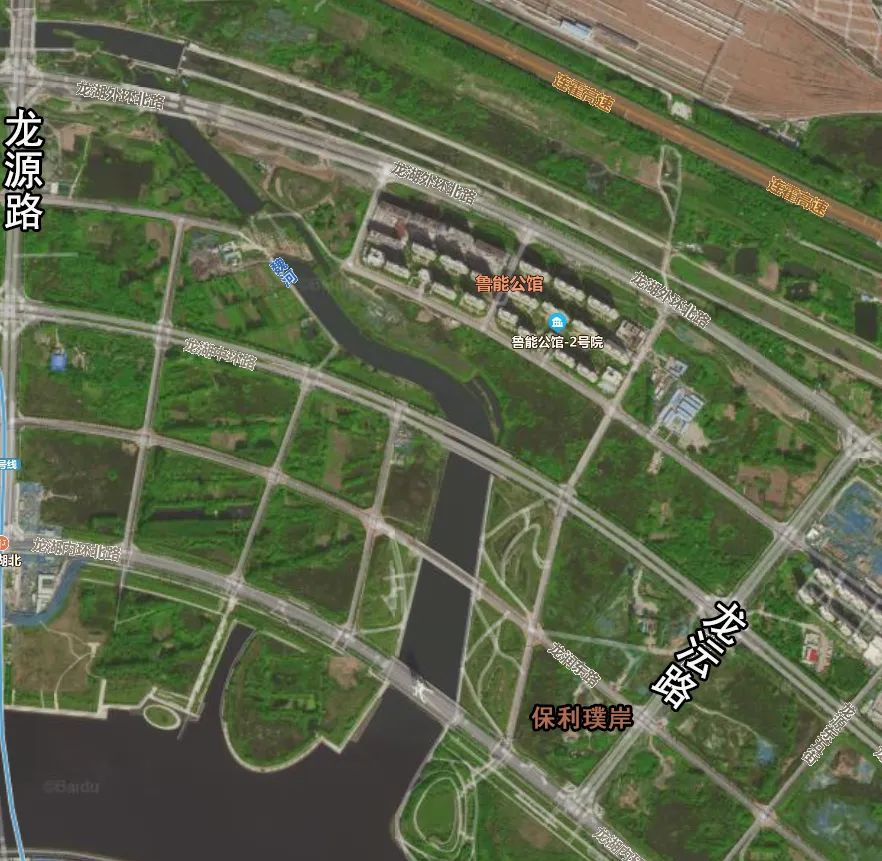
我认为AI的应用可能会增加转诊的数量,最好是必要情况下转诊至三级眼科医院,但不是假阳性结果转诊,尽管AI算法的操作阈值设置不当可能带来这样的问题。一些医疗保健系统可能尚未准备好应对这一问题,特别是在医疗保健系统中等待时间较长的国家。
12. 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存在哪些AI /深度学习的法规?在这一领域还需要做什么?
目前,美国FDA已于今年初发布了将AI算法用于医疗的指南。在指南中,它指出需要根据预期用途来提交和评估AI算法 。(URL:)另外,世界卫生组织(WHO)还发布了有关加强卫生系统的数字干预措施的推荐指南。(URL:)
13. 眼保健中AI /深度学习的下一步是什么?您对于有未来5-10年及以后的预期如何?
我希望在未来几年中将更多的AI算法用于临床,希望其中一些算法可以对患者的转归和就诊体验产生影响。深度学习在基因组学和蛋白质组学中的应用也令人兴奋,我也非常期待。 团队在2018年赢得了CASP( of ),此后,多个研究小组正在探索在相似领域中使用深度学习的方法。选择合适的靶基因或蛋白质可能会在新的治疗靶点上带来许多突破,并且可能会终止甚至逆转某些不可治愈的疾病。
14. 您认为您如何为中国眼科界做出贡献?
我一直觉得中国有很多非常努力的人才。我认为,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和区块链的时代,中国可能是开发医疗创新项目的最佳场所。就我个人而言,我祖籍福建,所以我与中国有很深的渊源。在西方国家(澳大利亚、英国、美国)的顶尖机构工作了10年以上,这使我熟悉了他们的文化。我衷心希望,借助与全球AI领域研究者的合作,我可以帮助提高中国眼科医生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同时,由于中国机会太多,我也希望在未来10年内重点关注和更多地了解中国眼科系统。我将很高兴认识更多的中国合作者,在中国建立更广泛的合作网络,成为中国与国际学术伙伴之间的桥梁。
My :
Email:

:
本文翻译团队
翻译:
梁嘉恩
高凯医生
熊健医生
宋云河医生
林凤彬医生
周柔兮医生
李飞医生:审校
欢迎留言区讨论交流
眼界:中国眼科医生的交流平台